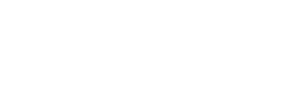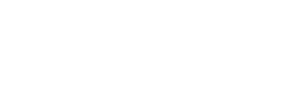民警如何鉴定“初次卖淫”?
2019-7-22
"生活所迫初次卖淫减轻处罚"的悖论?
作者:刘克军
为依法查处卖淫嫖娼活动,江苏省公安厅近日出台了“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”。这个从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: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,以及以口淫、手淫等方式初次卖淫嫖娼等情形,属于“情节较轻”的,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(6月1日《扬子晚报》)
我一向不反对法律容情和法外施恩,但前提是这种恩情应该施得合理,容得妥当,起码经得起推敲和检验。但是,“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者减轻处罚”这样的法规却让我产生了三个疑问,且实在是不吐不快:
首先,法律该不该对初次卖淫嫖娼行为容情?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:严厉禁止卖淫、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、嫖宿暗娼,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、警告、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,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这里面强调的“卖淫”是指“行为”而非“动机”,更非次数,不管她出于什么动机,都已经实施了卖淫这个“行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对卖淫行为的宽恕处理和容情其实就是对“执法必严”的破坏和践踏。再说,任何一个卖淫女都是由初次卖淫到无数次卖淫“成长”出来的,法律对他们的第一次“格外开恩”,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纵容,也难保他们不会发展到第二次甚至是第N次。
其次,“生活所迫”能不能成为卖淫的理由?搜索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,几乎所有卖淫女被抓时的解释都是“生活所迫”。应该承认,确实有个别卖淫女是因为生活所迫,但她走向卖淫道路的行为只能让人感到可悲但决不可怜悯。原因很简单:大多数残疾人尚且能够自立更深养活自己,这些年轻的四肢健全的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挣碗饭吃?穷不能成为卖淫的理由,同样不应该成为法律量刑的依据。
最后,如何鉴定“初次卖淫”与“多次卖淫”?“卖处”的少女算不算“初次”?恐怕未必。笔者31日还在《红网》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:3名少女用浸泡过鳝鱼血的海绵塞入体内冒充处女,以1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价格从事“卖处”活动达40余次,近日被株洲市芦淞公安分局庆云派出所抓获。警察如何分辨这样的卖淫行为?难道每抓一个卖淫女都要进行医疗鉴定和检查吗?恐怕即便检查也未必就能检查出时是“初次卖淫”还是“多次卖淫”吧?那么,难以检查又如何“从轻处罚”呢?
更可怕的是,个别警察一旦充分掌握了这一自由裁量权,恐怕江苏省公安厅“规范处理卖淫行为”的初衷将更加难以实现。此前,国内多次出现的“处女嫖娼案”无疑就是深刻的教训。如果江苏省公安厅出台这个措施,而无具体执行手段的话,恐怕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这样的闹剧反复出现:警察说谁是“初次”谁就是“初次”,说谁是“N次”谁就是N次,这样一来,打击卖淫嫖娼的执法行为岂不乱了套?
十年砍柴:什么是“初次”和“因生活所迫”?
新京报
最近,江苏省公安厅出台了“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”,其中规定“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等情形,属于‘情节较轻’的,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”(昨日《扬子晚报》)这说明我们承认有因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的,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对卖淫嫖娼行为,作为公共管理部门,当然应该采取尽可能坚决的态度、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击;对于社会道德来说,这也是一种应当被谴责的丑恶现象。对具体的卖淫者来说,其卖淫的理由千差万别,其人生的选择可能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。行政执法部门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等行为从轻处罚,体现了当地公共管理部门执法的人性化色彩,也体现“处罚是为了教育”这一目的,从这个层面说,这个规定值得肯定。
但这个规定在具体实施中,我担心会产生一些认定上的差异。比如说,什么是“初次”?什么是“因生活所迫”?
据我理解,“初次”应当是指卖淫被公安部门抓获的第一次,而不是实质上的第一次,因为判断是否是实质上的第一次实在太困难。而只有被抓获后记录在案,再次被抓才不是初次卖淫,这方面技术上还可以解决,最难界定的是“因生活所迫”。吃不上饭是生活所迫,那么失业算不算为生活所迫?卖淫者可以去端盘子而不愿意吃苦,去卖淫算不算生活所迫?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,对有些人来说不堪承受的艰难生活,对另外一些人也许是幸福生活。
判定一个人是否因生活所迫,其一般程序应当是:首先听卖淫者的陈述,然后调查其陈述的情况是否属实,最终由执法者进行判断。这就需要有个刚性的标准作参照,比如卖淫者个人属于何种状况符合“因生活所迫”,然后再去调查取证。出台这样一个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,而每一件案件去调查取证将极大地增加执法成本。那么就很可能使这一规定在实施中简化为:具体执法人员根据初次卖淫者的陈述,进行自由裁量。
这样就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,使具体执法人员以权谋私成为可能。因为是否是初次,是否因生活所迫,对卖淫者的处罚相差太大,几乎可以断定,所有没被抓获过的卖淫者,初次被抓肯定都说自己是“因生活所迫”,而来裁定这一说法是否成立的民警则权力太大了,因为即使是监督部门要判断办案民警的裁定是否公允,都相当困难,同时也不可能有利害人站出来举证某位卖淫者并不是“因生活所迫”。在目前的执法环境下,担心此规定扩充执法人员寻租空间不是毫无理由的。而且此举还可能对没有被抓获的卖淫者产生某种暗示:反正初次被抓,只要自己能被认定“因生活所迫”,处罚会很轻,那么会不会让一些没有案底的卖淫者胆子更大呢?
要不要严厉处罚卖淫者,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讨论的话题。但既然坚决打击卖淫嫖娼已经得到法律法规确认,在此前提下考虑执法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差异,体现执法人性化的一面,那么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其公正性的保障尤其重要。否则,仅仅加大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,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。